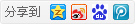一辈人接力一辈人,成就了今日之《辞源》,也将一种精神传承下来。这精神,倘若能借由“辞源”之源发散出去,渗透进各个领域,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,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。
100年前,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,发出了“国无辞书,无文化之可言”的呼唤,于1908年启动了《辞源》编纂工作,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。
100年后,2015年12月24日,历经8年编纂,《辞源》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。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,更是一种文化、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。
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。张元济,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,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,毅然投入“商务”1/4的资本编纂《辞源》,并亲自参与编写,只因为他深知在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面前,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,需要“开启民智,昌明教育”方能迎来光明时代。陆尔奎,第一版《辞源》的主编,2000多个日夜,罗书十余万卷,积累成疾,以致失明。而400万字的《辞源》,融旧学新知于一炉,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、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,得以传承复兴、发扬光大。1931年时,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,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。
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。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,需要找到新方法。《辞源》在编纂方法、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,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,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。尽管如此,“商务”出版人一直明白,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。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,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。于是,我们有了第二版、第三版的《辞源》,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,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。
这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。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,笑称自己是“遁入空门”,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。而《辞源》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每天做60张卡片,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,书未修完,惜人已半身不遂。第三版修订中,3位主编、22位分主编、127位学者,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,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,改动率达40%.
人们常说,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,可多可少,可深可浅,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,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,殊为不易,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。相比过去,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,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,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,更需去伪存真、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。如果没有一种精神,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?
8年的时间,足以写一部好的专着,留下几篇好的论文,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,他们中,最长者已有82岁,最年轻的35岁,每个人都竭尽心力,焚膏继晷,守护心底的追求。
第一部《英语词典》的编者塞缪尔·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,你想要惩罚谁吗?就让他去编字典。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: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,也不应判强制劳动,而应判去编词典,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。这言语中带着自谑,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。
吴泽炎曾说:“《辞源》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”,而辞源人的文化,也在一辈一辈的接力中传承下来。这精神,倘若能借由“辞源”之源发散出去,渗透进每个领域,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,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!